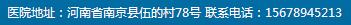阿坤有了第三颗心脏
广东首例移植心脏血管病变患者成功实施二次“换心”手术
3月9日早晨,阿坤出院。他特意定制了一块“仁医仁术大爱无疆”的木质牌匾,赠予我院。出院时,他说:“除了感激还是感激。我这是全国罕见的病,是你们给了我二次生命!”
现年39岁的心脏病患者阿坤,胸腔里正跳动着来之不易的“第三颗心脏”,第一颗是从胎儿时期陪伴他的“原装”心。
16年前,他因扩张性心肌病导致的心脏功能衰竭,换上由志愿者捐献的“第二颗心脏”。
年,由于“移植心脏”血管病变,他不得不再次“换心”。
近年来,阿坤几乎跑遍全国各大城市求医问药,却得到了不理想的回复:“想二次心脏移植排斥反应太严重了,难!”“这种情况,你只能保守治疗。”“只能考虑安上一颗人工的机械心脏。”
连阿坤自己都一度感到泄气。患心脏病多年的他,深谙其中的道理:“二次心脏移植排斥反应很大。控制不好,可能就‘人财两空’了。”
今年春节前夕,我院心胸外科主任梁毅却一手接下了任务,在电话里,他对阿坤说:“你来吧!只要匹配到合适的供体,我们竭尽全力帮你。”
求医坎坷
“医院都说没希望”
23岁那年,一场感冒迟迟不愈,医院。病毒性心肌炎往往伴随着感冒而来,这样的“感冒”,几乎所有重度心衰患者都曾经历过——每天憋气,一躺下就能感觉到那种濒死的窒息感。
所幸的是,年轻的阿坤不足半个月,就等到了“第二颗心脏”,迎来新生。
娶妻生子,阿坤经营着一个美满的家庭。年,年仅36岁的阿坤却发现,第二颗心脏也出现了问题——反复胸闷、气促,这些症状都与13年前接受心脏移植手术前相似,甚至更严重了。
梁毅说,在众多心脏疾病中,扩张型心肌病属于病因不详,且预后较差的那种。“我这是家族遗传导致的扩张型心肌炎,年轻时常常熬夜、抽烟、喝酒。生活习惯不够自律。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阿坤解释道。
彼时的阿坤经历反复多次住院保守治疗仍未见好转。“老家的医生说,我大概是熬不过一年了,除非再换一颗心脏。”阿坤看着一家老小,非常沮丧。
在全国的器官移植群里,他不断向病友打听消息,从上海、武汉再到厦门、北京去了大大小小6家医院求诊。在医学层面,心脏移植前,必须对群体反应性抗体PRA进行检测,这个指标很重要,与移植排斥反应和存活率密切相关。阿坤的PRA抗体呈阳性,指标达到91%。这意味着二次心脏移植排斥风险将会非常大。
医院曾建议阿坤,换上一颗人工心脏。一切救命的办法,阿坤自然都不会放过。他钻研过“人工心脏”,那是一个拳头大小的“机械泵”,通常情况下,它会被安在患者的心尖或者腹腔,用来代替左心室向全身泵血。
“但不适合我,我的第二颗心脏右心房上的血管病变硬化了。高频射的‘机械泵’可能导致我右心房的血管长期承压,容易破裂。”阿坤说,“人工心脏”只能是缓兵之计,过两年,依然要做心脏移植手术。
不少医生建议保守治疗。然而,不断吃药住院的阿坤发现,药越来越不起作用了。甚至长期吃药,导致血液淤塞在肠道里。肚子发紫,硬得像结石一样。严重的腹水和浮肿让阿坤的身体像一块吸满水的海绵。他常常感觉心脏是亢奋的,身体却是疲惫的。白天睡不醒,晚上睡不着。
“穷途末路了。北京、医院都说没希望。”阿坤坦言,“有时候想死,却又不甘心。老婆孩子我都放不下,活着压力又特别大!”阿坤一度变得沉默寡言。
年初,他忽然想起自己的姐姐,医院做过一次心脏移植手术。又把资料寄给了梁毅。“我猜想他也会拒绝我。”阿坤说。
然而,在电话里,曾经为百余位患者开展过心脏移植的梁毅,却一口答应了。他说:“你来吧!”
求生艰难
“国内成功的病例不超过10例”
“目前,国内成功的病例不超过10例。”梁毅说,阿坤的检查报告被反反复复地“咀嚼”着。查阅大量文献后,梁毅团队发现,因移植心脏血管病变而二次心脏移植的病例少之又少,最终成功移植的案例更是凤毛麟角。近30年来,国际上有据可查的同类二次心脏移植手术仅有30例,且均无文献记载。
对医院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对患者而言,求生何其艰难。
“供体难”是不言而喻的,这是心脏移植面临的一个世界性难题。这背后的原因极为复杂。一方面,移植的心脏供体需来自脑死亡但心脏仍然跳动的人。而在这类人中,还会因为年纪、心脏质量排除一大部分,剩下的合适供体少之又少。
另一方面,心脏是所有移植器官中保存时间最短的。在适宜温度下,心脏缺血时间不能超过6—8小时。此外,心脏对于供体匹配度的要求极高,例如一个矮小瘦弱的人无法给一个高大强壮的人提供心脏。这些严苛的要求,都令心脏移植的手术数量远远低于肝移植、肾移植。
《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显示,目前全国晚期心衰患者近万,而每年心脏移植的手术大约只有台——想成为万中的那个,实在是太难了。
所幸的是,大年初五,阿坤幸运地等到了匹配的心脏。
但是,这颗心脏能否被安全放入胸腔,还要跨过“排斥关”。对于阿坤来说,已做过一次心脏移植,身体免疫排斥比第一次移植的时候要厉害。阿坤的PRA即抗体较高,必须进行血浆置换。
手术前,阿坤已经被推入手术室。他的全血缓缓引出体外,分离成血浆和细胞成分。几乎以同等速度“竞跑”,机器用血浆代用品替代了阿坤的血浆,回输进阿坤体内。
“这是一步险棋。稍有不慎,满盘皆输。”梁毅说。
一切准备就绪,梁毅用手术刀细细划开阿坤的胸腔。虽然早有预案,但站在手术台上,梁毅仍然感到困难。
可见,阿坤的“陶瓷心”泛白发硬,紧紧地与整个胸腔粘连在一起。血管增生盘根错节、冠状动脉硬化,几乎让梁毅无从下刀。
“取心”非常困难。在术前,梁毅及团队曾反复多次与麻醉科、重症科、肾内科、内分泌等多学科讨论方案。一旦在“取心”过程中出现大出血,团队将立即采用第二或第三个方案。为保住阿坤的性命,ECMO团队也在手术台边候着。
然而,在梁毅、叶红雨、吴颖猛、黄伟钊几名经验老到的医生的通力合作下,胸腔内的血管与“陶瓷心”一点点地剥离开来,术中出血并不多。
“整个手术比以往多花了两到三倍的时间。因为患者心脏周围的生理结构已经发生改变了,心脏周围血管甚至已经损坏了。要顺利换心,我们只能一点一点地把血管和完好的心脏都接驳上。”梁毅说。
“成了!”数小时后,在阿坤胸腔里,心脏重新跳动了起来。梁毅缓缓松了一口气,终于不负重托。
性命相托
“医院不一样”
“医院不一样,真的不一样!病人心里清楚得很!”阿坤说。在我院住院期间,当他默默在被窝里沮丧流泪时,梁毅、叶红雨夜里完成手术,还穿着手术衣巡病房,拍拍肩鼓励他坚持。护士自掏腰包,给他卖水果送零食。看着阿坤郁郁寡欢,医院主动找来了心理科为他会诊。
“医院都拒绝我的时候,我就知道手术的风险有多大,但我信任中山市医院,也愿意以性命相托,放手一搏。”在出院当天,阿坤总是反复地说着梁毅当初的一番话:只要匹配到合适的供体,我们竭尽全力帮你。
梁毅说:“这是做得最艰难的一个病例。即便如此,我们也从来没想过放弃。更可贵的是,我们与病人相互信任,最终让病人活下来了!”
“人间真好,活着真好!我们可以去大口吃肉,去看陪伴家人,还可以看着孩子慢慢长大。”3月9日上午,看着即将出院的弟弟,阿坤的姐姐说。
3月10日中午2点40分,春日里的暖阳正好,阿坤已经回到老家休养。
此时,梁毅医生忙碌完,刚刚吃上午饭。
这一轮,医学获胜。
20世纪90年代起,中山便在全国率先开展器官移植手术。年开始,我院成功完成中山市首例心脏移植手术。数据显示,目前,我院一百余例的心脏移植患者中,70%的患者至今都健康地活着。
据国家医政医管局发布的“所器官移植医疗机构名单”,医院仅50余家。我院作为其中一家,除了心脏移植外,还开展肝移植、肾脏移植等,是国内获得器官移植医院。
当前,中山要建设国际高端医疗服务聚集区,布局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西翼国际医疗中心。我院在广东乃至粤港澳大湾区器官移植领域“异军突起”,这与我院多学科协作能力的提升以及在器官捐献协调方面所作的努力密不可分。
截至年3月4日,我市共完成器官捐献例,捐献心、肝、肾等大器官个,捐献眼角膜个,共救治患者名。百万人口捐献率全国地级市前茅。器官捐献产出率达3.74,年百万人口器官捐献率最达15.8,连续6年全国地级市第一。